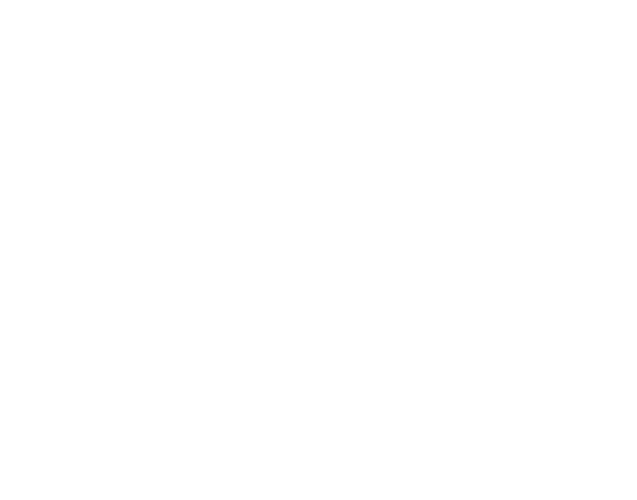王宇心 19管工3班
清晨,炊烟渐次升起又飘散,金黄色的阳光被院子里那棵无花果树的叶片切割的细碎,懒懒散散地撒落在窗棂上。瓦下厅堂里,外公躺坐在老摇椅上听着陈年的戏腔,轻声和着哼唱。
一切都是熟悉的样子,只是村民的长辈不再约着聚在一起搓麻将,每家的大门都紧紧地闭着,透不出一丝光;晒谷场上也看不到别家孩子们笑闹着追逐的身影,就连那条通往村子外的小路,也被一扇厚重的铁门拦住,显得有些寂寞。
外公的66岁庆寿宴原本是在正月初六,家里早商量好请城里的厨子过来烧流水席,邻居亲戚也已经请了百十号人。可是开年愈发严重的疫情把一切喜悦的希望冲得干干净净,父母只好撤了宴席,又打电话挨家挨户通知庆寿取消。外公靠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摇椅上,什么也没说。
自此,家里再也没有人提过那场被迫错过的寿宴。日子开始被愈发严重的疫情占据,村头的大喇叭每天播放着预防感染的措施,手机满里是疫情确诊人数不断跳动的曲线,我们为死亡人数下逝去的生命叹惋,看着疫情分布地图一块块触目惊心的红色黯然神伤。可是,病毒还是蔓延到了村子所在的县城,他露出锋利的獠牙,狞笑着告诉我们它的来临。
那天,县里确诊了两名肺炎患者并被送到县人民医院的消息在村里炸开。外公听到这个消息时慌了神,他跑过去抓起手机拨出一个号码,听了一段时间后颓然放下。焦急的左右走几步后又拨出同样的号码……
最终,晚上九点多电话被拨通,外公急急地喊了一声:“英子啊,你现在搁哪儿呢?”电话那头静默了片刻,低低地传来一声:“大哥,我在医院。”我静默地站在一旁,不知是不是错觉,我总觉得外公的声音似乎哽了一下。他轻轻地说:“我听说有两个得肺炎的送到你们医院去了?你得小心着点,那病染上了可不好治,你……” ,“护士长!”电话那头有人叫了一声,我听见姑婆模糊地应了一声,然后打断了外公的话:“哥,我会好好的,你放心。”电话被挂上,千言万语都被封在一阵冰冷的忙音中。
过了一个多月,姑婆与外公再一次通上了电话,外公絮絮叨叨的话中免不了埋怨:“医院那么多护士,你不能请两天假吗,你还当你年轻的时候啊,都一大把年纪了。”轻笑一声,姑婆接过话:“再老也是护士,也和其他护士一样。”, “每天量体温的时候都心惶惶的,咳嗽一声都心惊半天,但想想还是不能走。”
我总得对得起这身衣裳,姑婆说。
兄妹两人并没有聊多久,姑婆换班的时间快到了。临挂断电话时,姑婆跟外公说:“哥,你这六十六啊咱得补上。”“等着这日子太平了,一定要补上”。我似乎能看到姑婆说这话时的表情,她一定上扬着唇角,满心喜悦地期盼着那一天到来。
4月4日上午十点,这时我已经回到城市中的家,钟声被空气包裹着从遥远的地方传来,伴着马路上致敬的车鸣生叩击在我的心头。一时间,难言的激动在胸膛荡开,到底什么是英雄呢?我脑海中回忆起姑婆的样子,她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像一朵摇曳着盛开的山花,她说话的时候总是轻声细语的,眉目温柔,大概就是平凡至极的慈祥老太太的模样。可是,她认真又固执地说“我得对得起这身衣裳”的时候,又是那么的勇敢而不凡。大概这就是英雄的本质,我们生来平凡,平时早已习惯于淹没于人海,留恋于平淡的一餐一饭。可是疫情期间,外卖小哥穿上工作服在城市间为别人的柴米油盐穿梭;医生套上白大褂在医院为病人博一个未来的希望;警察身着制服守在关卡旁,以凡人之躯,抵制病毒的蔓延。归根结底,他们大概都像我的姑婆一样只为了一个目的:对得起身上的这件衣服。英雄,会感到害怕,可是对明天的期盼足以支撑他们向前走,哪怕是烈火焚烧,哪怕是地冻天寒,也依然是日夜兼程,依然是信念不衰。
我想,不会太久,外公会等到妹妹参加他那场寿宴;不会太久,大街小巷又是人声鼎沸。再等等,等着英雄归来,将春天带给我们。
到那时,卿云灿兮,山花满路。